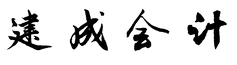出表,照旧不出表,这是一个问题。
通常,会计效果仅仅是被动反映经济现实,但在资产证券化领域,会计效果却在努力驱动生意业务结构的生长和演变。缘故原由很简朴,若是难以实现相关资产的会计出表,或许不少证券化生意业务便不会发生。
从效果上说,出表与否,不仅关系到资产欠债表上的偿债指标,也关系到利润表上的业绩指标。以证券化一组外币计价的短期应收账款为例,由于应收账款的一样平常核算不要求思量预期(但尚未发生的)违约损失、钱币时间价值、以及远期汇率升贴水,假设允许出表,这些先前在会计准则下安然“隐藏”的项目或将转化为资产处置损益,更不必说提倡人在证券化历程中自留的权益、提供的其他信用增级措施、外币及利率交换合约(若有)等项目需要作为单独的资产或欠债思量,其中部门项目还可能根据公允价值计量,由此增添了利润表上的颠簸,一言以蔽之,先前的一系列“会计幻觉”将由于出表而被打回真相;反之,假设无法出表,则往往视同抵押乞贷举行核算,除增添乞贷及利息支出外,一切依旧波涛不惊。
恒久以来,实务中存在一个有趣的征象——只管各人配合推行“实质重于形式”这一基本原则,但在详细问题上仍可能得出差别的结论——某些情形下,提倡人根据经济知识以为能够出表,但会计师却凭据准则划定以为不必出表、不能出表,或者至少不能所有出表(固然,另一些情形下也可能泛起相反的效果)。为了澄清常见会计问题上一些典型的误解,本文将限制出表的因素归纳成“四个没有”,希望对读者有所资助和启发。
要害词一:没有“资产”的资产证券化
×误解:“若是你有一个稳固的现金流,就将它资产证券化”
√正解:“若是你有一个稳固的现金流,就将它证券化”
各人都知道华尔街的名言,“若是你有一个稳固的现金流,就将它证券化”。但这里为什么只说“证券化”,而不说“资产证券化”呢?缘故原由或许在于,不少常见的证券化工具(“基础资产”)并不组成“(会计意义上的)资产”。
例如,对于“收费权”证券化(包罗高速公路证券化车辆通行费收入、水电站证券化发电收入、主题公园证券化门票收入等等),从会计的角度说,证券化工具是实现于未来时代的营业收入,只管代表了一项经济利益,但究竟尚未转化为条约收款权,因此不组成“(会计意义上的)资产”。
又如,对于不动产租金证券化,只管不行打消的租约通常讲明提倡人拥有条约收款权,但根据会计准则的划定,除非该租赁生意业务被归类为“融资租赁”,否则也不组成“(会计意义上的)资产”。
以上种种情形下,既然没有入表,也就自然谈不上出表,故由提倡人比照抵押乞贷举行会计处置惩罚。犹如禅宗所说的,“原来无一物,那边惹灰尘”。
要害词二:没有“转移”的金融资产转移
×误解:只重实质,不重形式
√正解:形式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形式是万万不能的
实务中存在不少对“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过分解读,其中之一就是将其片面明白为“只重实质(风险和报答),不重形式(执法形式)”。但事实上,根据金融资产终止确认规则,两者之间相互依赖,缺一不行。换言之,若是没有实现“形式上的转移”,纵然完成了“实质上的转移”,也同样无法出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急时代,有一种被称为“合成债务抵押凭证(syntheticCDO)”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形式颇为引人注目。该类证券化结构的特征是,提倡人设立根据自动导航原则运作的特殊目的载体(“SPV”),与其就特定贷款组合签署信用风险掉期合约(CDS),SPV同时向不特定投资者刊行资产支持证券举行融资,并将召募资金所有购置剩余限期与信用风险掉期合约相匹配的高信用品级、高流动性债券(例如,国债),一旦特定贷款组合发生坏账损失,SPV将立刻出售所持债券,并将接纳款子用于推行上述信用风险掉期合约。由于上述证券化结构并不要求将基础资产的所有权或现金流量转移给SPV,纵然通过信用衍生工具转移了贷款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答,也无法实现会计出表。
另一方面,只管转移的形式至关主要,却纷歧定要求组成“(停业隔离意义上的)真实出售”,后者在更大水平上是一个执法问题而不是会计问题。缘故原由在于,纵然提倡人未能转移金融资产的所有权(例如,通知债务人),或者将金融资产的所有权转让给可能不知足停业隔离要求的载体(信托企图以外载体的执法效力尚待视察),凭据金融资产终止确认规则,仍可能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之一来实现“(会计意义上的)转移”,一是“转移收取现金流量的权力”,二是“现金流量过手摆设”。其中,现金流量过手摆设要求同时知足“不垫款”、“不挪用”和“不延误”三大条件。
资产证券化中,提倡人可能不希望债务人(主顾)知晓债权被转移的事实,或者力争制止金融资产所有权转移和抵押物挂号等贫苦,故往往接纳“代持所有权+权力完善”之类摆设。某些情形下,提倡人将金融资产转让给不需要合并的SPV,代表SPV持有金融资产的所有权,并将现实收取的款子实时转付给SPV,同时约定,一旦债务人或提倡人泛起违约事项,提倡人必须立刻向SPV转移相关金融资产的所有权(即“权力完善事项”)。对于上述摆设能否知足出表的形式要求,实务中存在差别的看法,其中一种看法以为,参考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早先的讨论,除非提倡人转移了金融资产的“某一不成比例的部门(如最先收回的90%)”,否则通常可以视作提倡人转移了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力(仅仅是在权力完善之前无法反抗第三方);另一种看法则以为,在权力完善之前,SPV不具备(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债务人主张权力的能力,故不能以为提倡人转移了收取现金流量的权力,因此,能否知足现金流量过手摆设的要求便成为基础资产出表的要害。不外,后一种看法可能在实务中遭遇一个手艺性挑战——纵然提倡人仅仅负担了金额极其有限的差额支付义务或财政担保(这在资产证券化中并不鲜见),也可能由于未能知足现金流量过手摆设的“不垫款”条件而导致无法出表。
另外,应收账款、信用卡或小额贷款证券化中普遍接纳的“循环购置结构”可能组成出表的障碍。所谓“循环购置结构”是指,由于基础资产的平均接纳限期较短,相关方约定不将收回的投资源金立刻分配给投资者,而是由SPV再投资于提倡人的同类资产以维持资产池的规模稳定,云云循环往复,直至邻近资产支持证券的到期日为止。在此情形下,倘若提倡人因自留大部门次级权益等缘故原由而需要合并SPV,很可能导致基础资产在提倡人团体的合并财政报表层面上无法出表,主要缘故原由在于,合并抵销提倡人与SPV之间的内部生意业务后,“(会计意义上的)转移”仅可能透过资产支持证券以现金流量过手的形式发生在SPV与投资者之间,然而,由于提倡人团体未能将收回的投资源金实时分配给投资者,故无法知足现金流量过手摆设的“不延误”条件,因此仍不能出表。这里需要注重的是,合并SPV并不一定导致基础资产不能出表,仅仅是扩大了陈诉主体并响应改变了出表的手艺门路而已,上例中,出表失败的缘故原由并不在于合并SPV自己,而在于循环购置结构所固有的再投资摆设的阻碍,反之,传统的“过手摊还结构”中便不存在同类问题;此外,自留大部门次级权益也纷歧定意味着无法知足风险和报答转移的要求(缘故原由参见下一节),不外,既然没有知足转移的形式要求,能否知足转移的实质要求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总之,形式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形式是万万不能的。
要害词三:没有“变更”的未来现金流量变更
资产证券化实务中,出于控制资金成本等缘故原由,提倡人往往通过差额支付义务、财政担保或自留次级权益等方式为资产支持证券提供信用增级,这事实会在多大水平上影响到有关“实质(风险和报答)”的剖析呢?
×误解:风险和报答剖析中,企业应当比力转移前后该金融资产使其面临的“最大风险敞口”
√正解:风险和报答剖析中,企业应当比力转移前后该金融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净现值实时间漫衍的变更使其面临的风险敞口
关于风险和报答剖析的一个典型误解是,提倡人应当比力转移前后该金融资产使其面临的“最大风险敞口”。但事实上,根据金融资产终止确认规则,提倡人应当比力转移前后该金融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净现值实时间漫衍的变更使其面临的风险敞口(实务中通常以“尺度差”等指标权衡)。不难发现,相对于重大且稀有的“黑天鹅事务”,会计准则要求提倡人越发关注合理且可能的“较或许率事务”。
举例而言,提倡人将一组金融资产真实出售给SPV,作为信用增级措施,提倡人根据被转移资产金额的5%提供“限额财政担保(即限额以内的现实损失由提倡人负担,现实损失凌驾担保限额的部门由SPV及其投资者负担)”,根据历史履历和未来现金流展望,该组资产的预期损失率显著集中于【0—5%】区间。这意味着,只管提倡人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金额下降了95%之多,但在转移前后其所面临的未来现金流量变更却可能是没有或者较少“变更”的,也就是说,提倡人保留了被转移金融资产所有权上的大部门“(会计意义上的)风险和报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是严酷的限制,而且由此引出关于风险和报答剖析的下一个典型误解——若是提倡人保留了被转移金融资产所有权上的大部门风险和报答,则无法实现出表。
×误解:若是企业保留了大部门的风险和报答,则无法出表
√正解:若是企业保留了险些所有的风险和报答,则无法出表
事实上,根据金融资产终止确认规则,只有当提倡人保留了被转移资产所有权上险些所有的风险和报答时,才完全无法出表,而在其他情形下,仍可能实现某种水平的出表。其中,当提倡人既未转移也未保留险些所有的风险和报答但未放弃对基础资产的控制时(资产证券化中往往云云,参见下一节的讨论),会计准则要求根据“继续涉入所转移资产的水平”确认有关金融资产。举例而言,若是该继续涉入发生于一项限额财政担保,提倡人通常根据担保限额确认继续涉入形成的有关金融资产,这就是说,假设该担保限额占被转移资产的比例较低(例如5%),提倡人仍可能实现较大水平的资产出表。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应当怎样明白“险些所有”呢?由于海内和国际会计准则均没有明确划定,国际会计界在相关讨论中倾向于将“险些所有”明白为“90%左右”,也有一些会计师本着越发审慎的态度倾向接纳略低的比例。客观地说,这个比例越高,越有可能告竣出表的结论。借用一句圣经故事的名言,“天主关起一扇门,又打开一扇窗”。
要害词四:没有控制的“控制”
×误解:由于企业不再有能力自由地处置基础资产,应视为放弃了对基础资产的控制
√正解:若是转入方不能“自由地处置基础资产(即转入方能够单独出售资产且没有分外条件对此出售加以限制)”,那么,企业未能放弃对基础资产的控制
上一节中提到,假设提倡人既未转移也未保留险些所有的风险和报答但未放弃对基础资产的控制,会计准则要求根据继续涉入法处置惩罚。那么,若是提倡人同时放弃了对基础资产的控制又会泛起什么效果呢?会计准则提供的谜底很是明确——完全出表。
可能有好奇的读者会追问,资产证券化后,通常提倡人不再有能力自由地处置基础资产,参考合并财政报表准则中有关“控制”的观点,岂非不应以为提倡人已经失去对基础资产的控制吗?——这就是关于“控制”要求的典型误解。
事实上,凭据金融资产终止确认规则,判断提倡人(转出方)是否放弃了控制,应当关注转入方能否自由地处置所转移资产,即转入方能够单独出售资产且没有分外条件对此出售加以限制。
各人发现问题没有?金融资产终止确认规则所遵照的逻辑是这样的——只有证实“你控制”,才气推导出“我放弃了控制”,反之,若是不能证实“你控制”,纵然“我实质上放弃了控制”,也不能获得“我放弃了控制”的结论。
资产证券化实务中,通常SPV及其投资者等转入方同样无权单独出售基础资产,退一步而言,纵然转入方有权单独出售基础资产,但转入方思量到提倡人提供的种种信用增级措施后,也难免会在转售环节附加分外的条件(例如,提倡人对转入方提供了财政担保,若是转入方在转售环节未响应附加担保,则可能导致低价出售资产并遭受损失),因此,往往很难证实转入方获得了对基础资产的控制,也就不能得出提倡人放弃了控制的结论。
结语:没有实质的“实质”
会计喜好者往往喜欢将“会计判断”比作“悬疑推理”。阅读悬疑小说时,人们最爱问:“真相是什么”?钻研会计问题时,人们最爱问:“实质是什么”?但问题是,两者果真相同吗?
“真相”,通常指固有的、不随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客观事实:“实质”,往往取决于我们基于什么态度、针对什么目的、运用什么规则去界说它。若是我们愿意“跳出会计看会计”,暂时客串一下状师、投行或行业羁系机构的角色,就有可能在新的目的和规则下发现新的“实质”,或者说,发现“实质”并非那么唯一。现实上,当情境、视角稍作变换,前述“正解”未尝不是“误解”,而“误解”未尝不是“正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实质”都是有条件、有条件的,因而也是有局限性的。
事实上,当提倡人继续涉入被转移资产的风险和报答时,无论出表与否,都不外是强调了生意业务的“这一面”,而隐藏了生意业务的“那一面”。其中,出表的问题在于“该来的没来,不应走的走了”,即未能使用简朴直观的要领来反映提倡人在被转移资产上保留的最大风险敞口以及相关现金流量,更不必说无法体现提倡人因迫于声誉风险而自愿“刚性兑付”的可能;相反,不出表的问题在于“资产不像个资产,欠债不像个欠债”,即选择性地无视提倡人使用被转移资产的限制,以及债务的偿付以被转移资产为限的基本事实。以是说,“用力看,就是盲”,貌似对立的两方面现实上相互并存、相互依赖,原本是相通而浑一的,只有捉住这一要害,才气参透资产证券化的原来面目,从而顺应其无限无尽的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协调以上两方面的关系,新修订的金融工具列报准则参考国际会计准则的最新生长,专门针对“继续涉入已整体终止确认的金融资产”和“未整体终止确认的已转移金融资产”两种情形增补了详尽的披露要求,旨在通过增添披露的要领来应对金融资产终止确认规则的固有限制,以便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出经济现实。
由上可见,出表或不出表着实是一个庞大而玄妙的会计问题,究其根由,约莫是源于会计准则系统中“资产欠债表观”和“利润表观”这一对根深蒂固的矛盾。两者之间的冲突与妥协虽然增添了我们的痛苦和疑心,却也令我们越发理性和客观地看待问题,深切明晰人的局限性和无知,从而以包容和通达的心态去拥抱这个妙趣横生的天下。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崎岖各差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联合活动,详见哈尔滨会计代理 www.hrbsjgs.com